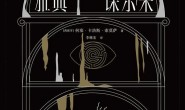简介
1692年的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沫……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
很快,恐慌蔓延至整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猎巫运动。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出卖彼此,牧师、富豪、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运动历时九个月,二十余人最终惨死,另有近两百人被指控为巫师。风浪平息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如今,“猎巫”一词已经成为刺激美国民众神经的文化符号,每当正义缺席,塞勒姆便宛如幽灵般闪现。 1692年的塞勒姆见证了一段为自保而彼此陷害的失智时期,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封闭的社会空间成为考验人性的试炼场,在偏见与矛盾的交织缠绕下,极端的正确最终沦为极端的错误。
作者介绍
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终身成员。早年曾在西蒙 – 舒斯特出版社任职,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
作品包括《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薇拉》《克利奥帕特拉》等,屡获好评和殊荣, 被誉为“当代美国最具诱惑力的非虚构散文作家”,2000 年获普利策奖。
2006 年,希夫获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授予学会文学奖,2019 年当选学会终身成员。2017 年,获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学会颁发历史及传记类终身成就奖。2018 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
部分摘录:
掠过橡树丛、长满青苔的沼泽以及纵横交错的溪流,安·福斯特乘着长杆,跨越了树梢、田野和篱笆。在她的口袋里,装着的是面包和奶酪。这是1692年5月中旬,潮湿的春天刚刚过去,空气中还弥漫着寒意。福斯特的杆子前头坐着玛莎·卡里尔。她的年龄只有福斯特的一半大,已是一位养育五个孩子的勇敢母亲,也正是她策划了这次飞行。她说服福斯特与她同行,并了解飞行的路线。向着东南方向,她们飞越伊普斯威奇河,飞过红枫林和百花盛放的果园,成片的草地和山丘在下面徐徐展开,清风拂过脸庞,一轮明月挂在空中。多年来,这对同为苏格兰后裔的近邻去的都是位于马萨诸塞安多弗的同一间教堂。
她们极速飞行,瞬间便穿过大片土地,这段路程需要一匹好马跑上三个半小时,而在不久前,这里的路面还遍布着石头,高低不平,在夜间无法通行。她们在飞行中也同样会遇到意外。前一分钟,她们还在空中,下一分钟就发现自己正在自由下落——在靠近密林时,她们乘坐的长杆突然折断,两人掉到地上。年老的福斯特双腿发软。她本能地张开手臂,紧紧抓住卡里尔的脖子。就这样,福斯特后来解释道——她的描述从始至终都一字未变——两人再次起飞,随后安全降落在塞勒姆的草地上。集会尚未开始,她们还有时间靠着树坐在草地上野餐,福斯特还去了附近的溪流跪着喝水。她们所遭遇的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例飞行故障。二十年前,瑞典的一个小女孩赶去参加一场草地上的重大午夜集会,在途中,她也突然从高空中掉了下来,摔得“身子一侧极度疼痛”。
福斯特和卡里尔在人烟稀少的地带飞行了十二英里 [1] 。没有人看见她们飞行,这倒是合情合理。可没人听见她们坠地的响声,这就让人吃惊。在新英格兰,声音会在空中回响和反弹,在人们的耳朵和想象中产生放大的效果。海狸用尾巴拍打河水的声音可以在半英里外听到。肥胖的黑熊“咆哮出的可怕噪音”会传向四面八方,就像绞刑台倒下时人群的尖叫声那样。每一场骚乱都得有个解释。内陆深处的海上巨响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一群鸽子飞落到了树上。那么怪异的低吼声呢?那是波士顿的塞缪尔·休厄尔家的奶牛发出的哀嚎,它被狗咬伤了。每个晚上,狗还会向着四处觅食的狼群嚎叫。但有时候,那疯狂的吠叫,那拂晓前树木折断的声响,表明了某种更为不祥的征兆。有时是邻居们正一块板一块板地拆除隔壁的房子,巧妙地解决着激烈的房产纠纷。可谁又会猜到,那听似洗衣妇在森林深处捶打亚麻织物的声音,竟会是巨龟在繁殖呢?
你也没有必要一定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候,夜间的拖步声和跺脚声是身着光鲜制服的外国人发出的。他们留下清晰可见的足迹,然后就消失在麦田、果园、湿地里。这些人可是全副武装,但经过神经紧绷的两周后,归来的六十个伊普斯威奇(Ipswich)民兵声称这是无中生有。人们认为那些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幻影。 [2] 这种解释要好过另一些解释。在夜间,你或许被一阵骚动闹醒,继而发现一窝欢腾的猫。明亮的月光很容易就照射出在窗上摸索的是苏珊娜·马丁,她撞向你的床,坐在你的肚子上,手伸向你的喉咙。安·帕特南的叔叔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布拉德伯里夫人消失在自家的院子里,几秒钟后又变成一只蓝色野猪重新现身。当那只小牛从烟囱落进厨房时,有个淘气的少年在附近悄然出没。那深夜壁炉里闪闪发光的水母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至少有十二只,吓着了埃利泽·凯泽。连女仆也看到了它们!母马前一分钟还在那里,后一分钟便消失不见。还有,在星期六的月夜,是谁移动了路标,让一个埃姆斯伯里的男人在离家三英里的灌木丛中蹒跚而行,又落入一个本不存在的大坑里?十八岁的苏珊娜·谢尔登揉了揉眼睛:一个茶碟自己飞出了门外。而那把放在苹果树下的扫帚又在做什么呢?
模糊的影像从黑暗中显现,分解成不同的实体。沙滩稍远处的那队人马其实是一个肩上扛着渔网的跛脚印第安人。休厄尔家里的小学徒在门外棒打一只狗时,他实际上是把棍棒对准了一个九岁男孩。塞缪尔·帕里斯牧师的奴隶提图芭撞上一头长着翅膀和长鼻的生物,它毛发旺盛,高达三英尺 [3] ,正在牧师家中一间暗室的炉火前取暖,提图芭便很自然地以为它的真身是坏脾气的莎拉·奧斯本。事实上,她发誓它就是莎拉。来自贝弗利的约翰·黑尔牧师的推测或许更为准确:当有东西掀翻烟囱,在屋顶上撕出八英尺大的洞,把白鑞器皿震得嘎嘎作响,又把他的手臂弄得麻痹不堪时,他猜测这是闪电所致。几位颇有名望的牧师试图协调感知与理解的关系,在一个4月的炎炎午后,他们在翻新的厨房里讨论为何“天上的大炮”格外钟情牧师的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是某处有人故意而为之的——就在这时,冰雹倾盆而下,撞碎崭新的窗户,砸落到地上。邻居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堆破碎的瓷砖和玻璃。它们隐约显露出某种启示。清教徒不会放过任何一场灾难。
在那次雹暴发生的三年前,安·福斯特就曾乘着长杆飞向塞勒姆。她不需要目击者来证实自己的空中遭遇,也有理由清楚地记得那次飞行的细节,甚至记得草地边沙径上的一串蹄印。此外,这次飞行还让她的脚伤了好几个月。
在新英格兰,有两种事物比这两个安多弗女人还要飞快。一是冲出森林并悄无声息地潜入村庄的印第安人。这些“可怕的方士和凶恶的巫师”,看上去他们才像是真正的黑暗之王 [4] 。无须敲门或打招呼,四个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就可能出现在你客厅的炉火旁一边取暖,还一边挑逗你,而你却只能拿着编织物缩在角落。你从波士顿旅行回来后,会发现你家已灰飞烟灭,家人也被俘虏而去,这一切都是拜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所赐。“找到他们比击退他们更为艰难”,科顿·马瑟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金发牧师如此写道。 [5] 他们躲藏着,潜伏着,飞快掠过,犯下暴行——然后又销声匿迹。甚至,他们的棚屋都能在一分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人看不见敌人,不能朝他们开枪。”坎布里奇的一位少将悲叹。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争端持续了五个月,直到1678年,菲利普王战争 [6] 才宣告结束。战争摧毁一百个新英格兰城镇中的三分之一,击溃那里的经济,夺走十分之一成年男性的性命。每一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居民——特别是塞勒姆所属的埃塞克斯县居民——都失去了朋友或亲人。1692年,殖民者将那恐怖的几个月称为“上一场印第安战争”,这是因为另一场战争已经显现端倪。一连串极具破坏性的袭击预示着同瓦巴纳基印第安人 [7] 及法国人的新冲突,在这场欧洲战争的延续中,法国人已和印第安人结盟。冲突的前线不久前已推移到距塞勒姆不足五十英里处。
谣言则化为另一名机敏的旅人,他潜入地板,飘过窗户,无视污泥、积雪和疲劳,迈着轻盈的脚步摆脱笨拙的真相。一个17世纪的书商认为,“全人类都爱打听消息,为此心痒难搔。”这种情况在缺乏报纸的时代更为严重,新英格兰人只能靠手头有的勉强凑合。消息无法穿过栅栏上的洞口或没有窗帘的窗户时,就要靠巧言来骗取。一对塞勒姆夫妇把他们的奴隶告上法庭,原因是后者监视他们,售卖他所了解的信息。考虑到共用的床和狭窄凌乱的住处——在塞勒姆,一个家庭平均有四个房间及六口人,还包括客厅的牛肉和厨房的织布机——就会知道隐私在新英格兰是稀罕物。不少马萨诸塞居民被咯咯的笑声唤醒,却发现这笑声恰是来自于自己的床上。
小城镇破坏了神秘之事与秘密之事的自然比例。在人口数不超过五百五十人的塞勒姆村,居民们了解前者多于后者。通过添油加醋和反复传播,传闻总是经久不息。1692年,安多弗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安·福斯特三年前曾遭遇一次严重的创伤。有天晚上,福斯特的女婿和女儿在土地买卖问题上起争执,最终做丈夫的割开了妻子的喉咙。当时,妻子正怀着两人的第八个孩子。谋杀者在绞刑架上忏悔,公开表明家庭和谐大有裨益。(这一说法亦是传闻,但至少出自牧师之口。)同样是在1689年,福斯特的孙子不可思议地从印第安人的伏击中幸存。他被剥去一部分头皮,本应命不久矣。福斯特的飞行伙伴玛莎·卡里尔在结婚前就与丈夫——一个身无分文的威尔士仆人——生下孩子,此事也搞得众人皆知。1690年,卡里尔一家患上天花。安多弗居民命令他们离开,他们拒绝了。当地的委员会便对卡里尔一家实行隔离,担心——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他们会“因疏忽大意而传播瘟热”。而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谣言称玛莎是一个女巫。
到了1692年1月下旬——那时,印第安人凶残的攻击把缅因的约克县夷为平地,让身负重伤的牧师死在自家的门阶上;那时,解冻期刚使新英格兰从异常寒冷的冬天复苏过来;有消息传来,在海的另一边,马萨诸塞的新总督亲吻了威廉三世的戒指,他将携带新特许状起航,有望让殖民地摆脱无政府状态——传闻不胫而走:塞勒姆牧师塞缪尔·帕里斯的一家很不对劲。
一开始是超过七个黑夜的刺骨疼痛。第一个遭受折磨的,是牧师十一岁的金发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很快,同样的症状出现在九岁的贝蒂·帕里斯身上。这对表姐妹抱怨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先是痛苦嚎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也感到眩晕。她们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又时不时变得僵硬。两个姑娘都没有发烧,也非患有癫痫。身体失去活动能力,双手却疯狂摆动。女孩们突然开始说“愚蠢、荒诞的话,她们自己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她们躲在角落,或钻到椅子和凳子底下,别人很难拉她们出来。其中一个掉到井中。阿比盖尔还试图飞到空中,她甩着手臂,发出飞起来的响声。两人似乎没有祈祷,虽然到了1月,她们又都变得乖巧懂事,彬彬有礼。一到晚上,她们睡得就像婴儿似的。
之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四个颇明事理的孩子——波士顿一个虔诚砌砖匠的儿女,他们“性情温和又举止得体”——患上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症。“他们像狗一样相互吠叫,又像猫一般咕噜叫唤。”科顿·马瑟在1689年观察约翰·古德温家的孩子后如此记录。孩子们像鹅一样飞扑着,有一次扑腾了二十英尺。他们躲避着无形的棍杖,尖叫着自己被刀割裂或被铁链禁锢。疼痛落到他们身上的速度超过了观察者能记录的速度。他们扭曲着身体,既不能穿上衣服,也无法脱掉。他们还试图扼死自己,下巴、手腕和脖子都脱了臼。“孩子有时听不到,有时说不出,有时看不见,而这三种情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马瑟记录道,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对青春期的完美定义。父母的谴责令他们极为痛苦,家务活也让他们厌烦不已。他们愿意擦一张干净的桌子,却对脏桌子毫无反应。家里的种种小意外都会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在世界上,”马瑟写道,“没有什么能像宗教活动一样让他们心神不安。”一提及上帝或耶稣,他们便会陷入“无法忍受的痛苦”。玛莎·古德温读得懂《牛津笑话集》(Oxford Book of Jests ),但每当读到证明女巫为杜撰的内容或马瑟的神学著作时,她便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个夏天,科顿·马瑟带走了十三岁的玛莎,帮助她恢复。她曾乘着她那匹“空气骏马”在马瑟家附近一路狂奔,在家庭集体祷告时发出嘘声,并攻击任何一个企图在她面前祈祷的人,她可以算是史上最糟糕的客人了。在同一季节,塞缪尔·帕里斯和妻子伊丽莎白搬到塞勒姆;正当他们还在熟悉这个村子时,在波士顿的玛莎把书砸向科顿·马瑟的脑袋。1692年,帕里斯本应立即想到古德温一家,并从马瑟那本不断重印、记录他们故事的《难忘的天意,关于巫术与附身》(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 and Possessions )中了解马瑟家的种种试验细节。他的牧师看过那些身体扭动的孩子,也支持书中的观点。“焦虑、扭曲、摔跤、颤抖、打滚、吐白沫”,这些行为也同样出现在这个塞勒姆家庭,而且情况更为严重。阿比盖尔和贝蒂哭喊着细针戳着她们的身体,皮肤像烧伤般疼痛。在一幢四十二英尺长、二十英尺宽的二层牧师住宅里,帕里斯一家无法摆脱尖叫声,这叫声从远处也能听到;他们唯一感恩的,就是这幢装有护墙板的尖顶房屋离道路很远。这家人的孩子还有十岁的托马斯·帕里斯和四岁的苏珊娜,两人未受折磨,却似乎都已惶恐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