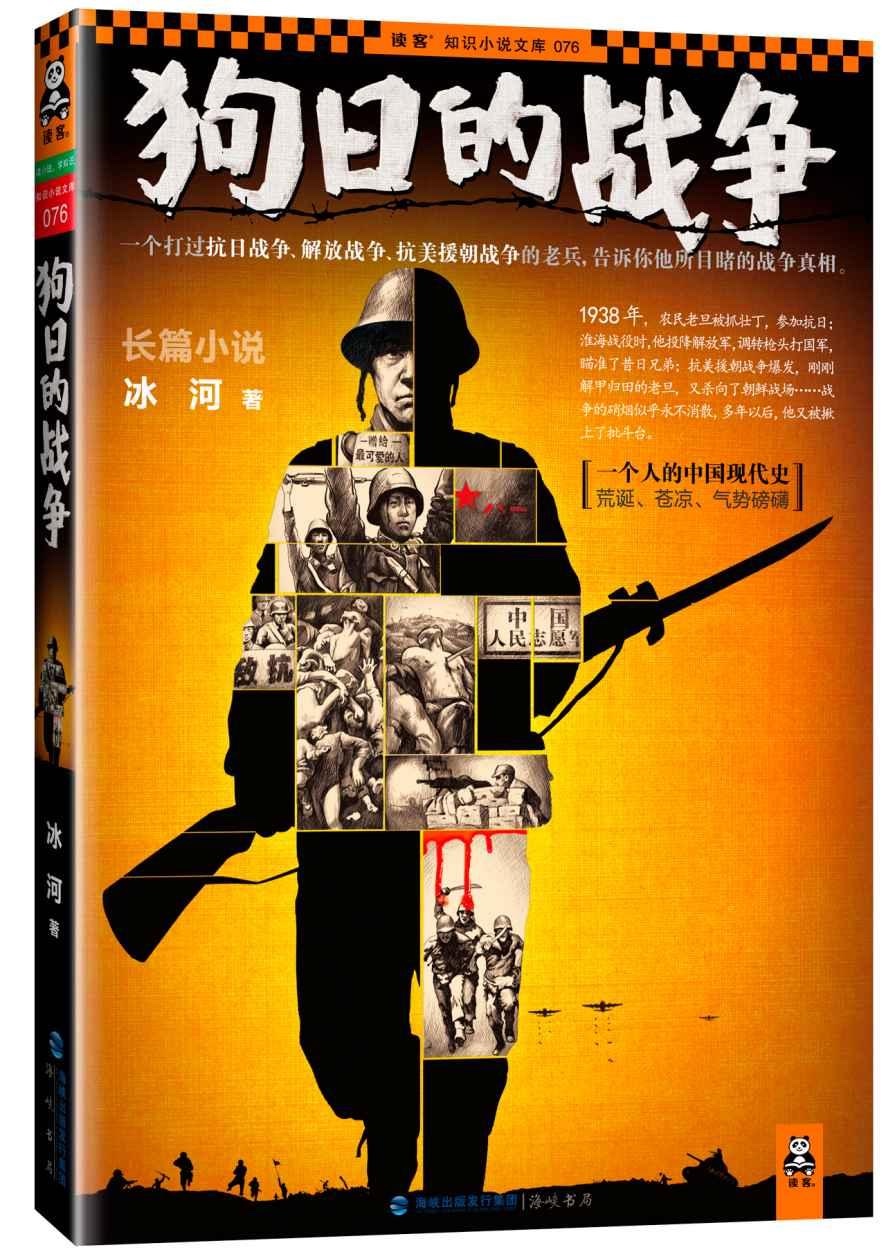简介
现代世界是在一连串的革命中形成的,从1776年的费城,到1789年的巴黎,再到1848年在欧洲惊天动地的社会灾难。
在1846年当选教宗并在意大利各地受到人们极度热爱仅仅两年后,教宗庇护九世发现自己实质上成了一个被困在自己宫殿中的囚徒。
席卷欧洲并震撼罗马的革命威胁要结束教宗对教宗国的千年统治,甚至要终结教廷本身。由此产生的精彩情节,伴随着一个个生动角色出场,从路易•拿破仑和他煽动人心的表兄弟查理•波拿巴,再到加里波第、托克维尔和梅特涅——故事中充满着背叛、悲剧和国际权力政治的纠葛。
大卫·科泽把这段关键时期的历史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介绍
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布朗大学社会科学小保罗·杜比(Paul Dupee, Jr.)校级教授、人类学系教授和意大利研究系教授,《现代意大利研究》合作创刊人及主编之一。曾任布朗大学教务长,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主席和美国欧洲人类学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意大利政治历史、梵蒂冈研究、天主教会和犹太人。科泽曾两次凭借年度最佳意大利历史著作获美国历史学会意大利历史研究会马拉罗奖(Marraro Prize)。其所著《埃德加多·摩尔塔拉的绑架》入围199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并已被改编成电影;《反犹教宗》入围马克·林顿历史奖(Mark Lynton History Prize)决选。
部分摘录:
如果那些在1846年选了不被看好的乔瓦尼·马斯泰·费雷提(Giovanni Mastai Ferretti)担任教宗的枢机主教们得知他将成为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教宗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在革命浪潮席卷19世纪中叶的欧洲时,教宗先是在意大利被赞颂为国民英雄、救世主以及上千篇诗歌和文章赞美的对象。但是在一刹那间,欢乐的赞美声就变成了“卖国贼”的怒吼,人们甚至高喊着要杀死教宗。这时是欧洲的变革时代。工业化打乱了旧秩序,交通工具的发展让革命如燎原之火蔓延各地,人们越来越怀疑以宗教为归宿的社会秩序。教宗庇护九世将在一瞬间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他将愈发感受到失控的恐惧。教宗本人是一个天性慈爱的人,他信仰坚定、虔诚,却缺乏理解正让世界发生转变的巨大力量的能力。在庇护九世(Pio Nono) [1] 的绝望中,现代意义上的罗马天主教会得以成形。
他将是最后一位教宗—国王(Pope-King),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双重角色和以教会律法为支柱的欧洲政治秩序即将崩塌。教宗在大地上的王国也即将崩解,这标志着欧洲变革已来到关键时刻,这场革命起源于100多年前开始传播的被统治者同意 和政教分离 的激进理念。这样的重大变革既不会轻易到来,也不会缺少付出流血的代价。
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标志着上百年来在欧陆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贵族政权开始谢幕。在那一年中,很多这样的贵族政权仍将存活下来,那些心慌意乱的统治者也能回到他们的都城,但此后的一切都已不再一样。神权和王朝统治的余年已经屈指可数,从巴勒莫(Palermo)到威尼斯的人民,从巴黎到维也纳的人民,已经陶醉地瞥见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不是作为臣民,而是作为被赋予了力量的公民。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跨时代变动要比在罗马来得更具戏剧性。罗马,这座“永恒之城(Eternal City)”是教宗国的国都。没有哪个城市发生的事会比在罗马城内发生的事件产生更大的国际回响,当大西洋两岸数以百万的天主教徒焦虑地追踪着教宗权威崩坏和他冒险逃亡的报道时,并没有什么人能预料到教宗权力的末日竟然如此的迫近。
*
庇护九世的前任是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此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是一名苦修士,生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一个地方贵族家庭,长着高耸的鼻子,嘴唇下弯,呈现着一副永远不变的皱眉表情。他脸上的恶性肿瘤疤痕让事情变得更为糟糕——摘除肿瘤给他留下了一个难看的伤疤。格里高利为自己赢得了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名声。他反对在自己的国境内修建铁路,也禁止臣民参加当时欧洲各地都在增加的科学会议。在他的眼中,教宗国被这样统治下去既恰当又合宜,但实际情况是国家腐败、管理失效,并且看起来他那300万愤怒的臣民并不会带来什么麻烦。 [2]
贫困包围着乡村,但奢华的16~17世纪的贵族宫殿和主教宫殿给许多罗马市民提供了工作。罗马民众并不认为贵族和主教之间具有多大的分别,这是因为这些主教通常是贵族们的年轻子嗣,而年纪大一些的儿子则会继承父辈的头衔和地产。几百年来,教宗们也常常出身于类似的家族。
虽然有富有的贵族、布满壁画的绚丽宫殿以及很多城市都拥有的宏伟教堂,但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却是一幅惨淡景象。城墙内将近一半的土地都无人耕种。点缀在这些荒地之间的是偶尔出现的一簇簇石松树和低矮的葡萄园,它们紧挨着被日光暴晒的古代温泉浴场、渡槽和教堂遗迹。蛇行流淌过城市的台伯河(Tiber River,也译“特韦雷河”)把城市分成小小的右岸和较大的左岸。右岸的北部坐落着梵蒂冈的宫殿,南部是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简朴民居。在左岸,坐落着罗马城的主要地标建筑和古代遗迹。沿着河岸,身披绿色斗篷的牧羊人看着他们的山羊吃草,喝台伯河发臭的黄色河水。而雨后,污泥会从罗马城破损的鹅卵石街道里渗出来,让步行甚至马车行驶变得危险。到访罗马的沙俄作家、社会改革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曾说:“你得习惯罗马,”并补充说,“它的优点并不明显。在城市的外面有一些老旧、陈腐、荒凉的地方;它的街道晦暗,宫殿阴郁。” [3]
穷人狭窄、潮湿的住所里没有灶台,所以人们要在户外生火做饭,这让街巷里充斥着水煮西兰花的刺鼻味道。美国雕塑家威廉·维特默·史都瑞(William Wetmore Story)回忆说:“猫在这里的穷苦人眼中是一种可口的食物。如果你有一只肥的,最好看紧一点,否则一定被偷。” [4]
从古代万神殿向外延伸的是错综复杂的狭窄巷弄,沿街上有露天肉市,市场里人头攒动,有各种营生。建筑物上垂下来很多绳子,女人将水桶系在绳子上,在肉摊的遮雨棚上拉动,各种商品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若不是垃圾的恶臭、灰尘、羽毛和洒在地上的脏水,也许这样的情景还能算是令人愉快。屠夫们在人群中挤开一条去路,他们穿着血迹斑斑的罩衫,手推车里放着在城根处宰杀的牛;而那些略小一些的牲口,如山羊、绵羊和猪则被放在了店外。鸡、火鸡、鸭子和鹅在禽栏里叽叽喳喳地叫着,男男女女坐在附近拾掇禽肉,把它们的羽毛剔下来扔到一个大篮子里。当他们把每只禽鸟拾掇完,便会向它们的嘴里吹气,使身体肿胀,然后再挂起来出售。
在星期三和星期六,巨大的椭圆形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上会聚集起罗马主要的蔬果摊贩,市场里的顾客摩肩接踵,他们精打细算地挑选当季食材。蘑菇会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多年来毒蘑菇已经让不止一位枢机主教身亡,其他身亡的人还包括许多微不足道的罗马市民。现在,任何蘑菇在出售前,都会有一名罗马官员给袋子盖上许可印章。
剃头匠也会出现在市场里,罗马到处都是露天营业的剃头匠。当顾客坐下来准备刮面时,剃头师傅会用挂在椅子后面的皮条把剃刀磨得锃亮,随后手脚麻利地完成工作。下一位顾客,正牙疼得要命,有可能会在这里拔牙,如果感觉不适,也可以在这里接受放血疗法。 [5]
但是最让那些来到这座永恒之城的访客目瞪口呆的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成群的乞丐——这种事在欧洲其他城市随处可见——而是无所不在的教堂和司铎(priest,即神甫)。有17万人口的罗马城,约有400座教堂,大多数都有着富丽堂皇的装饰。这些教堂里可能有3500名司铎和修士(monk),同时还有1500名修女(nun),她们大都住在修道院里。教会的职位早已五花八门得令人眼花缭乱。许多托钵会(Mendicant Religious Orders) [6] 修士几乎让人无法将他们和浑身发臭、衣衫褴褛的乞丐分辨开来,那些乞丐会央求路过的人能够施舍。对比之下,上层圣职(upper clergy)则是教会中的王公贵族。他们住在灯火辉煌的地方,占据着政府中所有的最高职位并控制着最好的农田,这些土地会出产占据教宗国一半的农业财富,然而他们却不用交税。高级教士(prelate,也称“教长”)掌管着公共金库,但他们把这些财产视作教会而不是公众的。他们还掌管所有的学校、法庭和警局。“一位枢机主教,”据法国大使观察,“在罗马是王公,在乡下是地主。”
至于下层圣职(lower clergy)——司铎、修士、托钵僧(friar)和修女——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大部分情形下,他们来自卑微的家庭,没受过什么教育,尤其是在偏远之地,他们的生活也是相当贫困的。国都的堂区司铎则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们享有部分来自宗教婚姻和政治权威方面的权力。当人们在罗马的街道上遇到一位堂区司铎时,男人们会脱帽致敬,女人和小孩则会亲吻他的手。这些司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进入堂区内的任何一间房子以检查教会圣训是否得到了遵守。他们雇佣探子并命令警察搜查住家、抓人,进而把胆敢冒犯的人拖去地牢。那些被关押的人通常在好几个月之后才被带到法庭里,到时在他们面前的法官本身也是司铎。在这样的法庭上,堂区司铎的证词就像是福音书一样被对待。罗马市民可能会被指控犯有通奸、鸡奸,或是辱骂他人,或是没能在大斋期间守住肉戒等罪行。所有的这一切,当然了,不会让圣职得到人民的爱戴,也不会让人们支持他们口中的“圣职统治”延续下去。 [7]
堂区司铎是罗马街道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戴着毛茸茸的黑色三角帽,帽子边沿处向上折叠,在头顶上方形成一个沉重的伞形。他们穿着系有明显扣环的黑鞋,露出小腿上的黑色短裤,身上有黑色的及膝长袍,扣子一直扣到肚子。为了增强效果,还有很多人拿手杖,手杖的上头有一枚亮闪闪的金属头。这样的司铎仍旧属于下层圣职中的精英人士。其他人,普通的司铎和修士则带着妒忌的眼光仰望上层圣职。他们是圣职中的最下层,和教宗国的底层人民一样,对教会精英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心怀愤恨。 [8]
当枢机主教们乘坐奢华无比的马车穿过大街小巷时,他们会路过那些遍及各地的乞丐身旁,这些乞丐在每一个街角、每一座广场、每一尊纪念碑和每一处教堂门口乞讨,他们也在餐厅门前乞求施舍。据一位法国的访客观察:“没有什么地方的乞丐比罗马的更愤世嫉俗、厚颜无耻。他不是在要求你的帮忙,而是好像他有权行乞,他总是以圣母的名义提要求,或是以最神圣的圣物的名义,或者是以炼狱中灵魂的名义提出行乞的要求,当他亲吻手上拿的盒子上的圣母像时,他要求你行善举,就好像你欠他什么似的。” [9]
然而,虽然罗马市民愤恨他们堂区司铎的权力和枢机主教铺张的财富,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虔诚信教的方式。每个住家和每家店铺都有圣母像,在圣母像的下面至少会有一盏从不熄灭的油灯。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虔信的某个圣徒,每个住家的户主都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当时的一个法国人观察道:“罗马市民,他们因习惯而践行宗教,他们害怕地狱,也害怕他们的堂区司铎,”他还补充说,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蒙骗一个外国人,或是在盛怒下杀死他的邻居,“至于缺席星期日的弥撒,或错过圣徒纪念日以及在星期五吃肉,则是绝不会发生的事儿。” [10]
*
历任教宗已经统治教宗国上千年,他们的领土范围曾经呈现过破碎、流动的状态,因此他们努力地运用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来扩大自己的领地。在格里高利十六世时,教宗国的领土从费拉拉(Ferrara)延伸到北方的博洛尼亚(Bologna),在东南方向囊括了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并由此包括了亚得里亚海岸的长条形地带,其中包括安科纳港(Port of Ancona)。从托斯卡纳以南位于意大利西海岸的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开始,教宗的土地一直向南延伸,经过罗马并囊括了一系列小城。在北边,教宗国与奥地利人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Kingdom of Lombardy-Veneto)接壤;在南边,则与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les)接壤。 [11] 总而言之,教宗国的领土只占今日意大利国土面积的14%,但是它位于半岛的正中心;而其300万人口中主要是不识字的农民,这些人以务农为生。
已经在欧洲北部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技术发明在教宗国里很少露面。这里很少有工厂,也没有火车。但是这种落后状态却属假性。几十年来,教宗统治的古老真理一直遭受着攻击。在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以及后来在拿破仑和法国军队影响的传播浪潮下,人们开始质疑是上帝制定了这种社会层级的观念,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此深信不疑,因而越来越愤恨享有特权的圣职和贵族。在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里,国王是上帝而不是人民选择的,因此任何打算推翻国王的企图都是逆天的亵渎和对上帝的攻击。但是有一种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政治理论正被传播开来。在这种思想观念中,最高权威并非源于统治者,而是源自人民。一个教宗—国王,掌控着军队和警察力量,已经越来越被人们看作中世纪的老古董。因为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信徒心中恰当的“圣父(Holy Father)”,对很多人来说,他没有当国王的职责,同样的,那些人也认为司铎们并不具有管理警察和法庭的职责。
和这种启蒙思想所推动的观念一道席卷欧洲的还有另外一种新的、强大的信条——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译“国族主义”)。当时的意大利半岛有很多分裂的国家,有如一块块的补丁,有各种王国、帝国领地和公国。许多这样的政权都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在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意大利应该得到统一,外国军队和外国统治者均不应该出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