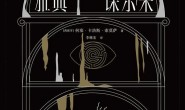简介
远山淡影(豆瓣评分8.2分)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技惊文坛的处女作,小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对故土、故人的回忆,讲述了战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与心魔,最终以母女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
浮世画家(豆瓣评分7.9分) 战后日本百废待兴,人们积极投身于重建未来中,画家小野看似闲云野鹤的晚年生活却潜伏着一股心灵暗流。为了给小女顺利出嫁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他开始重访故友,重温往事,让记忆回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那段时期。
长日将尽(豆瓣评分9.7分) 《长日将尽》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也是奠定其国际一流作家地位的重要作品,小说以“能代表英国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男管家为切入点,以现实主义手法入木三分地表现了英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的思想意识。”小说于1993年获翻拍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成为影史经典。
我辈孤雏(豆瓣评分7.2分) 英国伦敦,1930年代。年少得志的克里斯托弗·班克斯是全英国闻名遐迩的大侦探。然而,多年来,一桩未解的悬案却久久地在名侦探的心头挥之不去,那便是儿时他生身父母在旧上海滩的离奇失踪案。主人公从纸醉金迷的伦敦上流社会一路寻觅,最终回到了侵华日军炮口下的上海。等待着他的是一个黑暗的秘密,一个残酷的真相……
莫失莫忘(豆瓣评分8.7分) 《莫失莫忘》是石黑一雄一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借主人公凯西之口探寻过去记忆的真相。英格兰乡村深处的黑尔舍姆学校中,凯西、露丝和汤米三个好朋友在这里悠然成长。他们被导师小心呵护,接受良好的诗歌和艺术教育。然而,看似一座世外桃源的黑尔舍姆,却隐藏着许多秘密……
无可慰藉(豆瓣评分8.4分) 小说描写一位钢琴演奏家在一座谜样的城市里所经历的谜样的几天。他忽而是旁观者,忽而又被卷入其中,所见之人无不一往情深却又执迷不悟;所遇之事无不怪异荒诞,充满变数。
小夜曲(豆瓣评分7.9分) 《小夜曲》是石黑一雄的一部短篇集,全书以音乐为线索,由五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故事的主要人物都同音乐情牵相关: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多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却满腹牢骚。
被掩埋的巨人(豆瓣评分8.0分) 公元六世纪的英格兰,本土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似乎已走到了终点,两个族群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但与此同时,一片“遗忘之雾”充盈着英格兰的山谷,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他们的生活好似一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于是踏上了一段艰辛的旅程。
作者介绍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1995年英女王授予石黑一雄文学领域的大英帝国勋章,1998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7年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但石黑一雄却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是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他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在开创一个新的格局,横跨了欧洲的贵族文化、现代中国、日本,乃至于1990年代晚期的英国生物科技实验,而屡屡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
部分摘录: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神秘的咒语把我们两个定住了。天越来越暗,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远处河边的那个影子。突然间,咒语解除了,我们两个都跑了起来。跑近时,我看见万里子缩成一团侧躺着,背对着我们。佐知子比我早一点到那里,我怀着孕,行动不方便,等我到时,佐知子已经站在孩子身边了。万里子的眼睛睁着,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死了。但是后来我看见她的眼睛动了,用奇怪的、空洞的眼神盯着我们。
佐知子单腿跪下,扶起孩子的头。万里子还是那么盯着。
“你没事吧,万里子?”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到。
她没有回答。佐知子也不做声,检查着她的女儿,把她在怀里翻来翻去,好像她是一个易碎的、没有感觉的洋娃娃。我发现佐知子的袖子上有血,再一看,是万里子身上来的。
“我们最好叫人,”我说。
“不严重,”佐知子说。“只是擦伤。看,伤口不大。”
万里子躺在水沟里,短裙有一面浸在黑色的水里。血从她大腿内侧的伤口流出来。
“怎么了?”佐知子问她女儿。“出什么事了?”
万里子还是盯着她妈妈看。
“她可能吓着了,”我说。“现在最好别问她问题。”
佐知子扶万里子站了起来。
“我们很担心你,万里子,”我说。小女孩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转过去,走了起来。她走得很稳;腿上的伤看来并无大碍。
我们往回走,过了木桥,沿着河边走。她们两个走在我前面,没有说话。我们回到小屋时,天已经全黑了。
佐知子把万里子带进浴室。我点燃主室中间的炉子泡茶。除了炉子,刚才佐知子点亮的一盏吊着的旧灯笼是屋子里唯一的亮光,屋里大部分地方都还是漆黑一片。角落里,几只黑色的小猫仔被我们吵醒,开始骚动不安。它们的爪子在榻榻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再次出现时,母女两人都换上了和服。她们进了隔壁的一间小房间,我又等了一会儿。佐知子的声音透过隔板传了出来。
最后,佐知子一个人出来了。“还是很热,”她说,走过房间,把通向走廊的拉门打开。
“她怎么样了?”我问。
“她没事。伤口没什么。”佐知子在拉门旁坐下来吹风。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报告警察?”
“警察?要报告什么呢?万里子说她爬树,结果摔倒了,弄了那个伤。”
“这么说她今天晚上没有和什么人在一起?”
“没有。她能和谁在一起呢?”
“那个女人?”我说。
“哪个女人?”
“万里子说的那个女人。你现在还认为是她编出来的吗?”
佐知子叹了口气。“我想不完全是编的,”她说。“是万里子以前见过的一个人。以前,她还很小的时候。”
“可是这个女人今晚会不会在这里呢?”
佐知子笑了笑。“不会的,悦子,不可能。不管怎么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相信我,悦子,说什么有个女人,都是万里子发难时的小把戏。我已经很习惯她这些小把戏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编这些故事呢?”
“为什么?”佐知子耸了耸肩。“小孩子就喜欢做这些。悦子,你自己当了妈妈以后也要习惯这些事情。”
“你肯定她今天晚上没有和什么人在一起?”
“很肯定。我很了解自己的女儿。”
我们都不说话了。蚊子在我们周围嗡嗡叫。佐知子用手掩住嘴打了个哈欠。
“你瞧,悦子,”她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日本了。你好像不是很在意。”
“我当然在意了。而且我很高兴,要是这是你所向往的。不过不会遇到……很多困难吗?”
“困难?”
“我是指,搬到另一个国家,语言、习惯都不同。”
“我明白你的意思,悦子。但是说真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瞧,我听说过很多有关美国的事,对美国并不完全陌生。至于语言嘛,我已经会说很多了。我和弗兰克都说英语。我在美国住一阵子后,就能像美国女人一样说话了。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知道我能行。”
我微微鞠了一躬,但没说什么。两只小猫朝佐知子坐的地方走来。她看了它们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当然了,”她说,“有时我也在想事情会怎么样呢。但是真的”——她对我笑了笑——“我知道我能行。”
“其实,”我说,“我担心的是万里子。她会怎么样呢?”
“万里子?哦,她没问题的。你了解小孩子。他们比大人更能适应新环境,不是吗?”
“不过对她来说仍是个很大的变化。她准备好了吗?”
佐知子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说真的,悦子,你觉得我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些吗?你以为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前没有首先考虑女儿的利益吗?”
“当然,”我说,“你一定会仔仔细细地考虑。”
“对我来说,女儿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悦子。我不会做出有损她的未来的决定。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了整件事情,我也和弗兰克商量过了。我向你保证,万里子没事的。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她的学习呢,会怎么样呢?”
佐知子又笑了。“悦子,我又不是要到深山老林去。美国有学校。而且你要明白,我的女儿非常聪明。她爸爸出身名门,我这边也是,我的亲戚都是很有地位的人。悦子,你不能因为……因为眼前的事物就认为她是什么贫农的孩子。”
“没有。我从来没有……”
“她很聪明。你没有见过她真正的样子,悦子。在眼前这种环境里,小孩子自然有时有点笨拙。但你要是在我伯父的家里头看见她,你就会发现她真正的品质。大人跟她说话时,她回答得清楚、流利,不会像很多小孩子那样傻笑或者扭扭捏捏。而且绝没有这些小把戏。她去上学,跟最优秀的孩子交朋友。我们还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老师对她的评价很高。她这么快就能赶上真是叫人吃惊。”
“赶上?”
“这个”——佐知子耸耸肩——“很不幸,万里子的学习总是时不时地被打断。这个事,那个事,我们又经常搬家。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悦子。要不是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万里子就能过上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应有的生活。”
“是的,”我说。“没错。”
佐知子可能是听出我的语气不大对,抬起头来看着我。当她往下说时,语气变紧了。
“我不用离开东京的。悦子,”她说。“但是我离开了,为了万里子。我大老远地来我伯父家住,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对我女儿最好。我本来不用这么做的,我根本用不着离开东京。”
我鞠了一躬。佐知子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头凝视着屋外漆黑的一片。
“可是如今你离开了你伯父家,”我说。“现在又即将要离开日本。”
佐知子生气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悦子?你为什么不能祝福我呢?就因为你妒忌?”
“我是祝福你的。而且我向你保证我……”
“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的,你为什么不肯相信?那里更适合孩子的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我向你保证我替你高兴。至于我自己,我再心满意足不过了。二郎的工作很顺利,现在又在我们想要的时候有了孩子……”
“她可以成为女商人,甚至是女演员。这就是美国,悦子,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弗兰克说我也有可能成为女商人。在那里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相信。只是就我而言,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佐知子看着那两只小猫在她身旁的榻榻米上乱抓。有几分钟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我得回去了,”我打破沉默。“他们要担心我了。”我站起来,可是佐知子仍然看着那两只小猫。“你们什么时候离开?”我问。
“这几天。弗兰克会开车来接我们。周末我们就会坐上船了。”
“那么我想你不会再去给藤原太太帮忙了吧。”
佐知子抬起头来看我,冷笑道:“悦子,我要去美国了。我不再需要到面店工作了。”
“我知道了。”
“其实,悦子,要请你转告藤原太太。我不会再见到她了。”
“你不自己跟她说吗?”
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悦子,难道你不能体会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每天在面店里工作有多讨厌吗?不过我不抱怨,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现在都结束了,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地方了。”一只小猫在抓佐知子和服的袖子。佐知子用手背重重地拍了它一下,小家伙急忙往回跑过榻榻米。“所以请向藤原太太转达我对她的问候,”她说。“也祝她生意兴隆。”
“我会的。现在请原谅,我得走了。”
这次,佐知子站起来,送我到玄关。
“我们离开前我会去道别的,”我穿鞋时她说。
一开始这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梦;我梦见了前一天看见的事——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公园里玩。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同样的梦。其实,这几个月里,我做了几次这样的梦。
那天下午,我和妮基到村子里去时,看见小女孩在玩秋千。那是妮基来的第三天,雨小了,变成毛毛细雨。我有几天没有出门了,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户外的空气令我神清气爽。
妮基走得很快,每走一步,窄窄的皮靴子都咯咯响。虽然我也可以走得很快,但是我更喜欢慢慢走。妮基,我认为,应该懂得走路本身的快乐。再者,虽然她在这里长大,却体会不到乡下给人的感觉。我们边走,我边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她反驳说这里不是真正的乡下,只是迎合住在这里的有钱人的一种居住模式。我想她说得对;我一直没敢到英国北部的农业区去,妮基说,那里才是真正的乡下。尽管如此,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这些小路带来的平静和安详。
到村子后,我带妮基去我有时光顾的茶馆。村子不大,只有几间旅馆和商店;茶馆开在街角,在一家面包店楼上。那天下午,妮基和我坐在靠窗的桌子,我们就是从那里看见小女孩在底下的公园玩。我们看见她爬上一个秋千,朝坐在旁边长椅上的两个女人喊。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穿着绿色橡胶雨衣和小橡胶雨靴。
“也许你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我说。“我怀念小孩子。”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了,”妮基说。
“好吧,我想你还太年轻。”
“这和年不年轻没关系。我就是不喜欢一群小孩子在你旁边大喊大叫。”
“别担心,妮基,”我笑了,说。“我不是在强迫你生孩子。我刚刚突然心血来潮想当外婆,没别的。我想也许你能让我当上外婆,不过这事不急。”
小女孩站在秋千上,拼命拉链子,可是不知怎么,就是没办法让秋千荡得更高。但是她仍旧笑着,又朝那两个女人喊。
“我的一个朋友刚生了孩子,”妮基说。“她高兴得不得了。我真不明白。那小东西乱喊乱叫的。”
“至少她很开心。你的朋友几岁?”
“十九岁。”
“十九岁?比你还小。她结婚了吗?”
“没有。这有什么差别?”
“可是这样子她肯定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就因为她没结婚?”
“是的。还有她才十九岁。我不敢相信这样她会高兴。”
“她结没结婚有什么差别?她想要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计划好的。”
“她告诉你的?”
“可是,妈妈,我了解她,她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想要孩子。”
长椅上的女人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喊那个女孩子。小女孩从秋千上下来,跑向她们。
“那孩子的父亲呢?”我问。
“他也很高兴。我记得当他们发现他们有孩子了,我们全都出去庆祝。”
“可是人们总是假装高兴的样子。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部电影。”
“什么电影?”
“我想你没有在看。你在看你的杂志。”
“哦那个。那电影很烂。”
“是很烂。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肯定没有人在知道有孩子时会像电影里的人那样。”
“说真的,妈妈,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坐得住看那种垃圾。你以前都不习惯看电视。我记得以前我电视看太多,你总是叫我把电视关掉。”
我笑了。“你瞧,我们的角色变了,妮基。我相信你是为我好。你一定不能让我像那样浪费时间。”
我们离开茶馆往回走时,空中乌云密布,雨也变大了。我们刚走过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不多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喊:“谢林汉姆太太!谢林汉姆太太!”
我回头看见一个穿着大衣的小个子女人正急急地走过来。
“我猜是你,”她追上我们,说。“你最近好吗?”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你好,沃特斯太太,”我说。“很高兴又见到你。”
“看来又是坏天气。哦,你好,景子”——她碰了碰妮基的袖子——“我没注意是你。”
“不是,”我急忙说,“这是妮基。”
“妮基,没错。天啊,你长这么大了,亲爱的。难怪我弄混了。你长这么大了。”
“你好,沃特斯太太,”妮基舒了口气,说。
沃特斯太太住在附近。现在我偶尔才见到她,几年前她教我的两个女儿钢琴。她教了景子好几年,而妮基只在小时候教了一年左右。我很快就发现沃特斯太太的钢琴技术有限,而且她对音乐的总的看法也常常让我生气。比如说,她把肖邦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都称为“动听的旋律”。可是她为人和蔼可亲,我不忍心把她换掉。
“你最近怎么样,亲爱的?”她问妮基。
“我?哦,我住在伦敦。”
“哦,是吗?你在那里干什么呢?读书?”
“我其实也没干什么。只是住在那里。”
“哦,我知道了。不过你在那里很开心,是吧?这是最主要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开心。”
“那就好,这是最主要的,不是吗?那景子呢?”沃特斯太太转向我。“她最近怎么样?”
“景子?哦,她搬到曼彻斯特去了。”
“哦,是吗?听说那个城市总的来说还不错。她喜欢那里吗?”
“我最近没有她的消息。”
“哦,好吧。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景子还弹琴吗?”
“我想还弹。我最近都没有她的消息。”
沃特斯太太终于看出我不想谈论景子,尴尬地笑了笑,放开这个话题。景子离开家的这几年来,每次遇见我,沃特斯太太总是要问起景子。我很明显不想谈论景子,而且到那天下午都还讲不出我女儿在什么地方。但是沃特斯太太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很可能以后我们每次见面,沃特斯太太还会笑着向我打听景子的事。
我们到家时,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
“我想我让你丢脸了,对吗?”妮基对我说。我们又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花园。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说。
“我应该跟她说我正在考虑上大学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你说自己什么。我不觉得丢脸。”
“我想你不会。”
“不过我想你对她很不耐烦。你从来都不太喜欢她,不是吗?”
“沃特斯太太?哦,我以前很讨厌上她的课。无聊死了。我常常睡着,然后耳边不时有小小的声音,叫你把手指放在这里、这里或这里。是你的主意吗,让我上钢琴课?”
“主要是我的意思。你瞧,以前我对你期望很高。”
妮基笑了。“对不起我没学成。可这得怪你自己。我根本没有学音乐的天赋。我们屋里有个女孩是弹吉他的,她想教我几个和弦,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学。我想沃特斯太太让我这辈子都讨厌音乐了。”
“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重新爱上音乐,那时你就会感激上过那些课了。”
“可是我把学的全忘了。”
“不可能全忘的。那个年纪学的东西是不会全丢掉的。”
“反正是浪费时间,”妮基嘟囔道。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转向我说:“我想很难跟别人说吧。我是指景子的事。”
“我那样说最省事,”我答道。“她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想是这样。”妮基又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景子没有来参加爸爸的葬礼,对吧?”她终于说道。
“你明知道她没去干吗还问?”
“我随口说说,没什么。”
“你是要说因为她没有参加你爸爸的葬礼所以你也不参加她的葬礼?别这么孩子气,妮基。”
“我不是孩子气。我是说事实就是这样。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
我没有回答,我们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然后妮基说:
“刚才真是不自在,和沃特斯太太说话的时候。你好像很喜欢?”
“喜欢什么?”
“假装景子还活着。”
“我不喜欢骗人。”也许是我的话蹦得太快,妮基好像吓了一跳。
“我知道,”她轻声说。
那天晚上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妮基来的第四天——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今天晚上我换个房间可以吗?”妮基说。“我可以睡空房间。”我们刚吃完早餐,正在厨房里洗盘子。
“空房间?”我笑了笑。“这里现在都是空房间。你要睡空房间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你不喜欢你的旧房间了?”
“睡在那里我觉得不自在。”
“太没良心了,妮基。我本来希望你还把它当作自己的房间的。”
“我是这么想来着,”她急忙说。“我不是不喜欢那个房间。”她不说了,用干毛巾擦着刀子。最后她终于说:“是另外那间。她的房间。就在正对面,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停下手里的事,板着脸看着她。
“我忍不住,妈妈。一想到那间房间就在正对面我就觉得怪怪的。”
“睡空房间去吧,”我冷冷地说。“可是你得自己铺床。”
虽然我对妮基换房间的要求表现得很生气,但是我并不想难为她。因为我自己也曾对那个房间感到不安。在许多方面,那个房间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从那里看果园视野极好。但是很长时间里,它一直是景子极小心守护的私人领域,所以即使在她已经离开了六年后的今天,那里仍然笼罩着一股神秘的空气——这种感觉在景子死后更加强烈。
在她最终离开我们的前两三年,景子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她很少出来,虽然有时我们都上床睡觉后我听到她在房子里走动。我猜想她在房间里看杂志,听广播。她没有朋友,也不许我们其他人进她的房间。吃饭时,我把她的盘子留在厨房里,她会下来拿,然后又把自己锁起来。我发现房间里乱糟糟的。有发霉的香水和脏衣服的味道,我偶尔瞥见里面,地上是成堆的衣服和无数的时尚杂志。我只得连哄带骗叫她把衣服拿出来洗。最后我们达成共识:每几个星期,我会在她房间门口看见一袋要洗的衣服,我把衣服洗了,拿回去。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她的做法,而当她偶尔心血来潮冒险到客厅里来时,大家就都很紧张。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妮基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我没有见过景子在曼彻斯特的房间,她死的那个房间。作为一个母亲,这么想可能有点病态,但是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甚至在我感到震惊之前——是:在他们发现之前她那么吊着多久了。在自己家里,我们都一连几天看不见她;在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陌生城市里,更别指望会很快被人发现。后来,验尸官说她已经死亡“好几天了”。是房东太太开的门,她以为景子没有交房租就离开了。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画面的恐怖从未减弱,但是我早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病态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你就会熟悉最痛的部分。
“在空房间里睡我至少能暖和些,”妮基说。
“妮基,你晚上要是觉得冷,把暖气打开就好了。”
“我知道。”她叹了口气。“最近我总是睡不好。我想我老做噩梦,但是醒来后就想不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
“我想可能跟这里的安静有关。我不习惯晚上这么安静。”
“我梦见了那个小女孩。昨天我们看见的那个。公园里那个。”
“我在车上就能睡着,可是我不记得怎么在安静的地方睡觉了。”妮基耸耸肩,把一些餐具扔进抽屉里。“也许在空房间里我能睡得好一点。”
我跟妮基说起这个梦,在我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也许表明我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肯定从一开始就怀疑——虽然不确定是为什么——这个梦跟我们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没多大关系,而是跟我两天前想起佐知子有关。